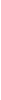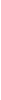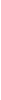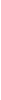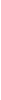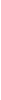随身带着淘宝去异界 - 373|种地日常
“我想加入你们。”
他对那位年轻的领袖说。
然后对方点了点头, “好的。”
于是接下来……
又是一个清晨来到。
安萨路睁着眼睛,定定看着还泛着青绿的棚顶, 直到起床的钟声传入棚中, 他才懒洋洋地和棚子里的其他人一块爬起来。他们打着呵欠,挠着肚皮, 抓着耳朵, 一个个走到屋外, 对着檐下的一个木桶拉开裤绳, 在淅淅沥沥的放水声中, 安萨路想着今天的早餐。
天气还是很热, 多人混居的草屋也远远不如旅舍的房间舒适, 但也不算难以忍耐, 就安萨路睡过的地方来说,这些草棚既通风,又没啥虫子, 同住人大抵身体健康, 每天洗澡换衣,连外面的尿桶都要日日倾倒洗刷,比起山洞、草窝、牲口棚、露天原野和树杈子之类, 岂止是不差, 在个人的一些琐事上,甚至能比肩老爷们的一些享受了。虽然洗澡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但水很清凉,又有专人来清洗和修补衣裳, 回到草棚,打开水罐,就能见到清澈无比的净水——外邦人不仅去掉了水中的泥沙和微虫,还坚持将水煮沸之后才给人饮用,虽然总有人觉得外邦人什么事儿都麻烦,但干这些费力活的人既能拿到报酬,喝水的人又只劳拿起杯子伸出手,最重要的是,腹痛确实少了。
腹痛少了,人就能吃得更多。哎,说起外邦人有什么能让人死心塌地的地方,首先的、毫无疑问、无人能比的,就是他们的食物。
第一,他们慷慨,十分地慷慨。吃饱这种在其他地方已成奢望的事,在外邦人这儿简直天经地义,只要你干活,并且能接受外邦人对食物的做法——第二,若非自己便是受益者,任谁知道外邦人如何处理食物,都是要大叫败家子的;藜麦一定要去壳,磨得细细的,揉成面饼后还要放到它们自己胀起来,然后放进铁的炉子里烤得松松的,透透的,烤到离着八百步远都能闻到那股教人抓心挠肝的香味儿;蔬菜只要嫩尖儿,老根和黄叶都扔掉,连菜干都是煮得软绵绵,嚼不出渣滓的;汤里一定要放肉,一些时候是银鱼干和去骨的鱼块,一些时候是新鲜的、剁得细细、同样不带骨头的净肉;家禽家畜剔出的骨架用来煮汤,煮到汤水从无色变为淡白,就捞出来放进烤炉里用余烬烘干,然后倒进筐子捧出来给人磨牙吸髓。第三,外邦人的食物能治病。
许多人都声称是自己因为这些丰富又精细的食物病痛全消,耳聪目明,外邦人也不如何以此表功,只说许多病痛都是因为人吃得不够,吃得不好,但不论过去还是如今,便是人都明白这些道理,又有什么用呢?既不是每个村庄都有磨坊,村头的烤炉一个月能开两次便是老爷的恩典,吃肉在丰年都得看运气,当下灾荒时节,谁舍得吃这样细净的白面?哪怕是在本地人的世代忆里,也只有外邦人能把粮食从老爷们的地窖里挖出来,并且把它们毫不吝惜地喂进每个人嘴里。
自然也会有人忧心忡忡,依外邦人的大手大脚,这些存粮未必能支撑多久——何况人还在源源不断地朝这座城市来呢。但已经很有一些人因为这些恩典而认为外邦人无所不有,无所不能,那么粮食自然也不成问题,而这种念头不得不说是很有根据的,毕竟外邦人连建筑所需的材料都舍得用船运来,谁知道他们的仓库里如今放了多少东西?
安萨路同其他人一起来到农地食堂。同城市内的工地食堂差不多,这儿的食堂也是砖石柱子撑起来的一个大棚子,平整的泥地上摆着成片的长桌长椅,穿着罩衣,布巾盖住半张脸的厨子和厨娘站在一排巨大的带盖木桶后面,手里握着勺子,拿着夹子,不声不响把食物均匀地分到每一个人的碗里。他们来得不早不晚,饭桶前已经排了一些人,安萨路抓了一副餐具站到一个队伍的尾巴上,目光落到别人的盘子里。
哇哦,又是新东西。
在饮食这件小事上,要说作为旅客和苦工两种身份感受到的最大区别,安萨路认为是食物的品种不同。虽说旅舍提供的食物在水路上颇有声名,不过那是外邦人舍得耗费食材,除了油脂丰厚,糖和盐特别纯净,以及烹调手段十分精细外,材料并无特殊之处,外邦人又允许外来的厨师去观看他们那个巨大的厨房,连菜谱都肯公开分享,所以人们自然而然地以为这便是他们的饮食习惯了,很少有人会想他们连食物都是异端。安萨路用自己的舌头分辨,自他成为一个农垦工的七日以来,至少五种食物他闻所未闻,至于那些调料、香料和酱料里又有多少古怪东西,那简直天知道。
倒不是安萨路认为这有害,毕竟他也是靠生吃蛆虫熬过一段岁月的,只是若说这是因为外邦人总同他们的苦工一处用餐,所以对食物也不另作区分,这岂能只用暴殄天物形容——这些愚昧粗俗的下等人知道什么是香料吗?他们的鼻子能分辨食物的风味吗?他们疏松的牙齿能用研磨来鉴赏肉质吗?他们被青盐渍透的舌头,能尝出晶糖同蜂蜜的不同,对他们不应有而享有的一切,又说得出一句恰如其分的赞美吗?
落座的安萨路抓着松软芬芳的面包咬下一口,又舀起一勺绵软浓稠的杂粥,眯起眼睛,在清甜中感受那些金珠般的饱满颗粒在齿间绽裂的口感。温柔的清风从田野吹来,穿堂而过带走暑热,近百人聚集在这里,却没有多少说话的声音,几乎所有人都吃得十分珍惜。也许在外人看来,这些叛逃的农夫根本没有吃饱的资格,但连牲畜都晓得草料的好坏,老爷们再愤愤不平,外邦人也不听他们的呀。
所以,安萨路想,那些比贵族修剪胡子还要精细地耕作过的田地里,外邦人究竟要种什么东西?
吃完早饭之后的餐具也不必自己收拾,食堂的巡视人不止管排队、打架、浪费食物和打破碗盘,餐具也是由他们一并收放到箩筐,等待别人送去洗刷。这些心满意足的农夫只需挺着肚子站起来,鱼贯离开食堂,走进晨日,去下一个地方。
集合点的草棚下,农垦队的队组长们和工具一同等待着。上工的钟声响起前,每个人都记了本册,拿到了自己的工具,然后踩着钟声前往今日的份地。
仍是这般空阔的景色,只是走在路上的安萨路已经是另一种身份,他扛着农具走在人群中,耳朵听着别人的低声闲谈,眼睛随意浏览,开阔的路面是泥土夯实,再铺一层取自城墙的碎石,由钢铁怪兽推碾到结为一体,就算闭着眼走也不会绊倒,路脊隆起,路肩微低,路基下便是清波荡漾的水渠,探头看去,甚至能看见一些游动的鱼影。只是田野空空荡荡,满目发白的土坎土块,若是遍布郁葱,眼前定然是一幅赏心悦目的美景。不过在此之前,安萨路很少,或者说几乎没见过这样纯粹的土地,不管农民还是贵族的田地,野草总是拔不完的,就算畜力充足,他们也耕不了这么深,至于翻沟起垄之类的细作,即便是队里年纪最大的农夫,也没听说过这世上还有谁这样折腾土地的,现在还什么都没种下呢。只是外邦人的异端之举也不止这一样两样,农夫们也只是私下嘀咕,不会有人指手画脚,一些人更是认为外邦人的一切举动都大有深意——看看他们干过的和正在干的事情吧。
安萨路并不迷信外邦人,但他也很难不这么想。
出了一点汗后,他们来到了地块上,管理田区的队长扎下了彩旗,道路上也驶来了马车的长列。马尾后的拖板上,一个又一个的滕筐摞得整整齐齐,将这些筐子卸下后,发现里面全是巴掌大,圆饼一样的黑色玩意。农垦队的成员把它们拿在手上,闻一闻,看一看,跟土坷垃较了这么久的劲,他们总算看到了点新东西,有人还偷偷用舌头舔了舔,然后队长告诉他们,今天要做的事就是把这些肥饼埋进地里。
“肥饼?什么是肥饼?”
“就像人要吃喝那样,这是种给粮食吃的东西。”队长说。
还没完全明白这是什么东西,农夫们便为话里的另一个意思兴奋起来:“什么?要种粮食了?”
“我们要种什么?”
“种子在哪儿?”
农夫们七嘴八舌地问,队长大声回答:“种什么很快就知道,明天就会送到!”
然后他们便都安下心来,自觉站成排看队长和组长是怎么干活的。队长和组长干完了,又对他们再三重复干活的两个技巧,一直到点名的所有人都点了头,才让他们两两结对,挎上筐子,拿起工具,走下田沟,沿着土垄一段一段挖出浅坑,埋下肥饼。
安萨路不曾当过农民,但外邦人差不多是把所有人都当做傻瓜来指导,教导的方法又大多闻所未闻,他学得很快,手脚又麻利,虽然他半路入伙,还是个不爱说话的大块头,也很快就被这支队伍里的其他人接受了。他们对他没有什么戒心,会在他身边谈论任何话题,即使那是因为外邦人对此没有任何禁制,安萨路还是会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他们竟敢将自己当做这些土地的主人之一。
这些农民是联合起来向外邦人交出了他们的土地,然后得到今日的身份,一支三到五十人的队伍中,大多数人出自同一个村子或农庄,像这样的队伍在整个农垦大队中有好几支。外邦人在拿走所有老爷的公地后,又要求近郊和远郊的农民同样让出他们的份地,这一蛮横的要求因为交易条件极其优厚,实际并未遭遇多少抵抗。毕竟春季水灾后,大多数田地已经指望不上收成,外邦人既声明只是租借这些土地,保证成熟季节至少分给他们一般年份的完全收成,又提出雇佣他们来种植这些土地,不仅付给报酬,还供应住所和饮食,连他们的家人也一并接入城中,那么大概只有决心去死的人才能拒绝得了,在那样一场胜利后,没什么人会想要同外邦人作对。
虽然外邦人也有一些为难的要求,例如他们的契约不接受单个的人或者单个家庭,最少要三个家庭共用一个名义,并且每一个人都得在一式四份的契书上按下指纹。收起契书后,外邦人便依契约上的名字来分配成员,父母和子女,兄弟和姐妹,亲属邻里大多能在同一支队伍中,这大大减轻了他们最初的不安,至少在见到那些钢铁怪物后,瑟瑟发抖地跟家人抱在一块总比不认识的人强得多。不过见到外邦人毫无区别地推平所有田界后,他们又有点觉得自己受了欺骗。
他们如何再找回他们的土地?
于是外邦人让他们抓阄,抓到哪一份,那块田地在契约上就“属于”他们了,由他们耕种,耕作的收获也照契约之数交由他们分配,当然,如果有人实在不能接受,外邦人也可以给他和他按过手印的那份契书上的全部人分一笔钱,很大一笔钱,然后客客气气地把他们打发出城去——似乎并没有这样大胆的傻瓜出现。
其实除了那份还留在契书上的收获,这些农人没有得到更多的东西,他们和那些被编入队伍的“外人”吃一样的东西,穿一样的鞋子,使一样的农具,干一样的活,却并没有什么不满。没有外邦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在春季死去了,便是不交出土地,他们也不敢说自己便能整家熬过饥荒,哪怕契约是骗人的,但一日三餐不是骗人的,新衣裳,新鞋子,新帽子,新农具,新房子,这些也是真真切切的,再说起奴役,他们在过去不一样要给老爷们干活吗?何况给外邦人干活也算不上多么辛苦。他们没有被当做牛马来使唤,最要出力的活儿是他们的钢铁怪物去干的,除了捡拾石块,抛撒粉末之类的手活,不管清理杂草杂树还是挖田沟,还是如今的种肥饼,都有便利的铁农具帮忙。
活儿干起来轻巧,渴了淡盐水管够,午饭不仅送到地头,吃完了还能在草棚宽大的檐影下小睡一会,直到被叫起来上课;下午的活儿干完了,又能去农地食堂好好吃喝,真是做梦都想不到种地竟然能这么舒服。没有鞭子和辱骂责打,那些管教他们的队长和组长也是要干活的,甚至绝不比他们干得少。这样的日子谁还要怨恨,那他定然是个坏了心肝的人,因为若是谁不想干好事,其他人都要受到连累。他们这些老实的农民还没出过事,但已经听说城里有人又懒又馋还欺负别人,被外邦人收回本册赶出去了。
真是活该。
这种时候不要外邦人的庇护,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活下去呢。那些人一定是被魔鬼迷了心窍,不然,哪怕只为了食物也该舍不得走呀。
斜阳西照,下工的钟声传遍城内城外,田地里的农人直起发酸的腰骨走上田埂,短暂的集合后,依旧是手握旗帜的队长在前,提着扛着农具的农民跟随在后,一群群一队队,从大地的各个方向向主道汇聚。外邦人像棋盘一样雕刻大地,这些自觉或不自觉展现出秩序的农夫农妇看起来也好似活的棋子。在安萨路这样纯粹的外人眼中,甚至从他们身上看出了一点军队的影子。
服从命令,彼此配合,进退有序,再看看他们手中的铁器,一把把都是分量沉实,当当作响的好货,并因为频繁使用而边锋雪亮,再加上良好的伙食,让他们的体质在短短一个月中有了明显的改善,如今要说他们只是普通农人已经有些勉强了。安萨路不确定那位年轻领袖让他必须首先来这里的用意是否为了让他看到这些,但外邦人的手段越是了解,便越令人感到可怕。
可怕不仅在于他们繁多的花样和不计代价的投入——只是食物便能在别地收买多少东西!更在于外邦人毫不掩饰、毫不留情的对一切“传统”“习俗”“规矩”,对几乎所有世俗常理的颠覆和抛弃。这种叛逆体现在他们的言语,行动,饮食与秩序,体现在旧城市的毁灭,新城市的孕育,在日日添加的一砖一瓦,在仍在延伸的平坦田野,以及那些无孔不入的文字与数字,以及面向所有人的,强迫性的学习中。
吃完晚餐洗了澡,天色还未完全暗下,还有余力的人大多不会去睡觉,日间的劳作除非受伤或是病了,不然是不能不去的,大家拿到的报酬也几乎没有区别,但在夜班上课前,少年人可以去指定的场所和同龄人玩耍,外邦人教了他们不少游戏的方式,男人们可以去兄弟盟学木工和泥瓦工,女人们则是去姐妹会,那儿也有人教她们女人的事情——虽然安萨路听说实际上两边给他们准备的东西是差不多的,在他们适应那些工具后,有些小活发下来,完成了就能有额外的收入。
再然后,夜班的铃音就会响起。
安萨路浮光掠影地观察这座城市时,认为自己看到的已经足够多,直到真正进入他们的生活,他才惊觉自己的浅薄——外邦人竟能做到这地步!当薄帘放下,魔力的灯光堂皇点亮,他同其他人一起坐在长椅上,掏出自己的本册放到桌面,看一名外邦人走上讲台,对这些农夫农妇说:“大家晚上好,我是今天的老师。在开始学习之前,大家回答我一个问题:我们学习,是为了什么?”
“为了我们变好,为了大家变好!”人们这么回答道。
安萨路感到了真正的吃惊。
这显然是一句被灌输的口号,但人们已经回应得习以为常,并且认为至少有一半是对的,因为外邦人已经做到了这一半。许多人失去家园来到这里,过上了比灾荒之前还要舒适的生活,几乎没有人想要失去这一切,所以外邦人要他们服从,他们便服从,但除此之外他们不会改变自己。外邦人显然不想见到这一点。只要人不改变,一座城市毁灭,重建起来的仍是相似的东西,外邦人无论多么特殊,他们总是少的,他们想要建立和维持的秩序终会在人性不变的自私怠惰之中迅速腐朽,然而一旦——只要他们对平民进行广泛的、持续的教育,事情便会有大有改变。
所以,一切金钱与物资的倾注都不如外邦人在教育上的付出更令人震撼。
而他们的讲课又颇有讲究,一小半时间他们是在宣扬功绩,不是直接自我吹嘘,而是首先表扬来到夜班的人们完成了多少的工作,然后说今天又有多少人来到这座城市,又出窑了多少石砖,又挖好了多长的沟渠,又铺好了多长的道路,哪里的工地活儿干得又快又好,又是谁在这些成果中因为做得好而受到奖励,而这些人又是什么出身,曾经受过什么样的痛苦,这些痛苦是谁造成的,他们得到奖励之后的期望又是什么,如此种种。有时候也会说谁犯下了不可原谅的罪过,要受到什么惩罚。外邦人叙述这些也不用鼓动的语气,但人们自然会去倾听自己关心的事,而这些言语也不仅仅是要告诉他们城市发生的事情,后半段要学习的生字同计算的题目同样来自这些讲述。
安萨路有一点点的基础,其他艰难学习的人对他表示羡慕,他自己却没有什么骄傲。外邦人的目标是一年内一千个通用词,一千五百个外邦文字,能够流利读出所有本册上的课文,能够自己写出一篇三百字以上的作文,能做一百以内的加减乘除……并且白天的活儿不会停。
天哪!你们在做梦吗?
今夜一样当堂完成了作业的安萨路看着寥寥几个被留课的倒霉鬼,有些不太确定这些宏伟目标是不是真的不能实现了。
随着下课的摇铃响起,这充实得令人疲惫的一日终于要结束了,安萨路拖着步子走出课堂,和其他人一同走在夜晚的路上。软风拂面,星光明亮,风灯在高杆上轻轻摇晃,不夜盲的人们在谈笑,在抱怨同展望,安萨路抻了抻腰,感觉到身后有人。
他放下手,脚步略略停顿。
“要动手了。”那个人低声说,同他擦身而过。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